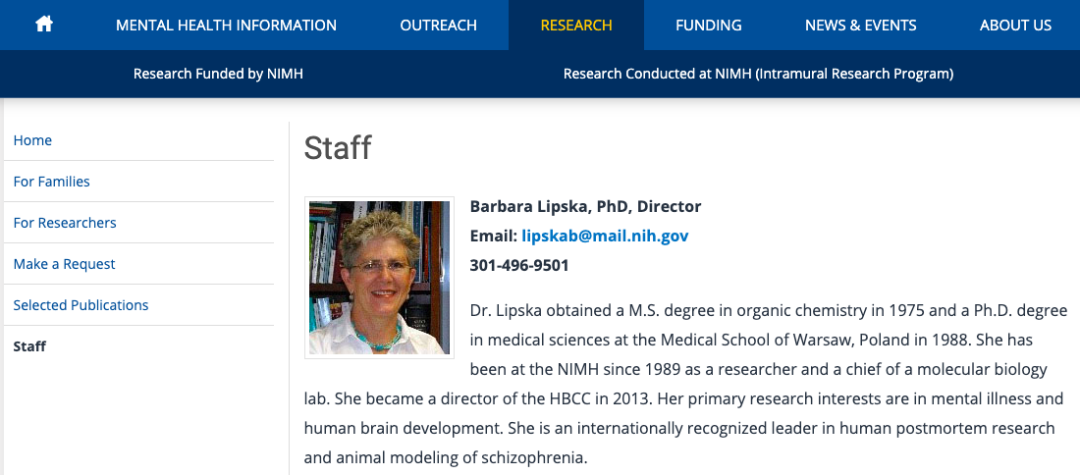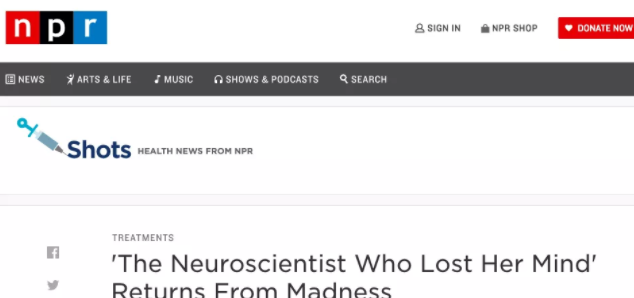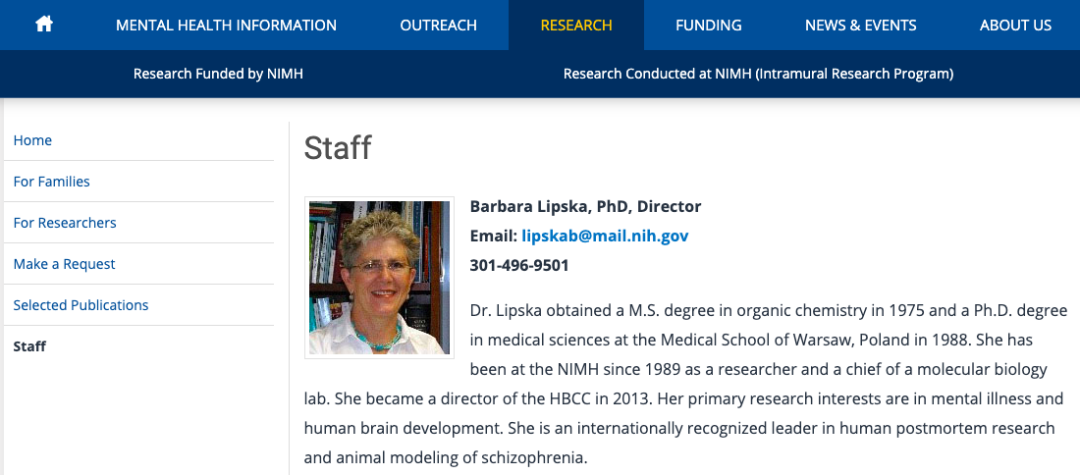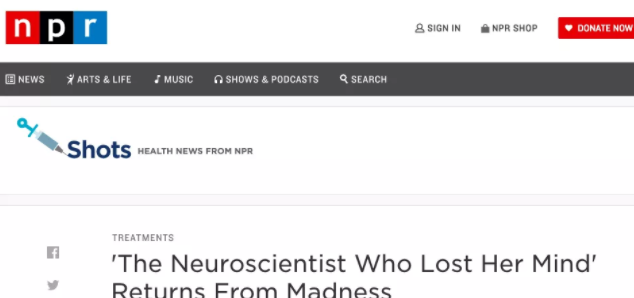毕生研究人脑的科学家,因脑瘤陷入疯狂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作为一名神经科学家和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 )人类大脑收集中心主任,利普斯卡博士以研究精神疾病患者的大脑为生。可以说,没有谁会比她更了解精神分裂症了。
而在 5 年前,她自己的大脑却得了病。
命运给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我身处在上千个大脑的环绕中,上千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大脑。
我叫芭芭拉·利普斯卡(Barbara K.Lipska),是一名神经科学家。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里,我一直在研究精神疾病。
我的工作与大脑为伴。这些形形色色的大脑因各种原因无法正常工作,有些大脑使人出现幻觉、听见神秘的声音、受到狂乱的情绪波动的折磨或者陷入深深的抑郁。过去 30 年来,我们对这些大脑进行收集、编目,并将它们存放到这里。
每份大脑样品送到我们这里时都是新鲜带血的,装在透明的塑料袋里,闪闪发亮,塑料袋小心地放在装着冰的保温箱里。它看起来像一团红肉,看不出与真正的人性有什么关联。但是仅仅在一天前,它还指挥着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人脑是进化到极致的产物,所有的褶皱、沟回、高低起伏,都有助于在头骨相对有限的空间内容纳更多的存储区域,并使脑能够行使更多的功能。
意识就是这种神奇而复杂的组织的产物,不幸的是,意识也会带来痛苦——精神疾病。
想要理解、治疗并在未来某一天彻底治愈精神疾病,研究人员需要研究大量的大脑。负责进行这些研究的正是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这类研究机构。在大脑银行,我们收集这些神奇的器官,将其切成可用于实验的组织样本,并与全世界的科学家共享。
我们获得的大部分大脑都来自附近的法医办公室的停尸间,哪里存放的通常是死因可疑或者死因不明的人的尸体。当一个大脑到达我们的大脑银行时,我们会先用数字对其进行编号,以便保护当事人及其家人的隐私,然后开始认真工作。
现在,我们可以将样品切开,研究其内部的工作机制,以便更好地理解精神疾病。
我的工作就涉及这些大脑,它们被切成组织块,并被冰冻保存起来,它们承载着乐观与希望:有一天它们将揭示大脑的秘密。
2015 年 1 月初,我决定参加铁人三项比赛。1 月将尽的一个星期二早上,在完成了第一届训练课后,我从游泳池出来,突然觉得头晕。
开车上班时,一种不好的奇怪感觉涌上心头。车开得摇摇晃晃,我却说不出哪里出了差错。我在办公室里坐下来,开始吃一碗从家里带来的燕麦片。我伸手打开电脑。
当我重复刚才的动作时,结果还是一样。每当我把手放在视野的右下方时,它就会完全消失,就像被从腕部全部切掉了一样。
我几乎被吓瘫了,一次次尝试着找回消失的右手。可是一旦把手放到那部分视野中,它就消失不见。这像是一种怪异的魔术,迷人、可怕,又完全无法解释——除非是……
我立即试图把这个念头赶出脑海。我确信自己在 2009 年战胜了三期乳腺癌,在 3 年前战胜了 1B 期黑色素瘤。但乳腺癌和黑色素瘤经常会转移到脑部。我知道,位于大脑后方、控制视力的枕叶出现脑瘤,是这种奇怪的视力丧失的最具可能性的解释。
我也知道,任何存在转移性(癌细胞扩散)的脑瘤都将是一个可怕的消息。
我试图遏制这种在我内心深处不断增加的恐惧,我告诉家庭医生,这肯定是眼睛的问题,眼科医生检查了我的视力后,发现我的视神经或视网膜没问题,也没有白内障。
「我担心问题出在你的脑子里。」她说,「你的枕叶皮层里肯定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做更多测试。」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去附近的一家成像中心做磁共振成像。前台人员为我办理登记,直到此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将要接受扫描,查看脑中是否有肿瘤。
恐惧让我有点恶心。一名护士在我的手臂上插入一条静脉注射线,在我的血液中输入了一些可被脑组织吸收的对比液。我在磁共振成像及其的狭窄管道里与嘈杂的声音一起,一动不动地躺了一小时,我已经完全精疲力尽。
我希望医生快点打电话,告诉我那个唯一可能的消息:不是癌症。
家庭医生在电话里说:「我很抱歉,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扫描发现你脑子里有三个肿瘤,你必须立刻去急诊室(ER),一个肿瘤正在出血,这很可能是黑色素瘤。」
在 2015 年初做完第一次手术后,为了防止大脑水肿,我服用了大量类固醇,这让我感觉自己像个超级英雄,充满无穷的能量。我成了一个被兴奋剂驱动着的疯婆子。我从波士顿给 NIMH 的行政、临床和科学主管发了一系列的电子邮件,告诉他们我死前想让他们知道的所有事情。这些电子邮件虽然内容合理,但数量很多,并且很长,非常详细,这是类固醇带来的躁狂能量的迹象。
现在是 2015 年,治疗癌症的最新也最有前途的方法是免疫疗法。这种前沿疗法可以调用身体自身的防卫功能来抵抗疾病,使免疫系统能够识别并摧毁在其他疗法下会成功逃脱的癌细胞。
关于使用免疫疗法有效治疗脑瘤的报告尚未出现,而最新的药物还没有应用于脑内的转移性黑色素瘤。据我所知,像我这种情况的患者注定没救。
3 月中旬,大约在我做完手术一个半月后,一系列磁共振成像显示多个脑区出现了新的小病变(组织异常的区域)。它们极有可能是肿瘤,尽管单纯从磁共振成像上很难认出来。
我的一位放射治疗肿瘤医生认为,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手术(SRS)是治疗肿瘤的最佳选择。对于患有晚期脑部黑色素瘤和有很多脑瘤的患者来说,SRS 是不可行的,因为需要进行高能辐射的位点太多了,这会造成危险的脑组织损伤。
幸运的是,现在我的脑中只有几个肿瘤,SRS 的靶向方法可能正适合我。
但靶向放疗并非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如果新的肿瘤继续出现(很明显会这样),我的大脑会挤满致命的病变。到那时医生会停止放疗,因为放疗已经无用了。大脑能承受的放射量有限,超过这个限度,就会造成永久性损伤。肿瘤会继续增长,压迫大脑,在狭窄的头骨空间内造成水肿。最终,我会进入昏迷状态。如果水肿挤压头骨底部的脑干,使我丧失呼吸的能力,我就会死去。
家人和我继续阅读医学期刊中发表的每项新研究。我们拜访波士顿的黑色素瘤专家、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收集信息,并分析他们的建议。麻省总医院的医生建议我先尝试免疫疗法,他告诉我,乔治城的阿特金斯医生指导开展了一项针对黑色素瘤脑瘤患者的免疫疗法临床试验。
4 月初,我听从医生的建议,给乔治城医学院的阿特金斯医生打了电话。
阿特金斯医生解释说,每 3 周会为我注入两种单克隆抗体药物的组合,以改善我的免疫系统。这些药物预计将教会功能失调的 T 细胞如何识别、攻击并杀死入侵身体的黑色素瘤细胞。
阿特金斯医生邀请我加入临床试验。但首先我需要做几件事,最重要的,是再做一次脑部磁共振成像,以确保除了已经进行过放疗的脑瘤外,没有新肿瘤出现。
如果有任何新的脑瘤,我就不能参加这次临床试验,至少现在不行。阿特金斯医生告诉我,试验不适用于脑内存在未经治疗的活跃肿瘤的患者。活跃肿瘤接受免疫疗法时可能会发炎,患者可能会出现严重的脑肿胀。
离试验开始只有几天,我被告知一切正常,我欣喜若狂。
一切都很顺利,直到那一天——我给我曾经的放射治疗肿瘤医生发了封电子邮件,告诉他我将参加免疫疗法的临床试验,并询问他是否可以查看下我的磁共振成像结果。
然而几天后,那位医生却告诉我:「我看到你的大脑里有新肿瘤。肿瘤很小,很容易被漏掉,但它们肯定存在。」
我完全无法接受这个结果。我本来计划明天开始参加试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我决定不把发现新肿瘤的事情告诉任何人,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参加这次临床试验。
第二次注射后不久,我的身体开始对我反戈相向。它不仅攻击脑部的肿瘤,还开始攻击全身的健康组织。这种自体免疫反应在我的皮肤、甲状腺、脑下垂体造成炎症。我的皮肤最让我遭罪,从头到脚满是瘙痒的红疹子。
此外,免疫疗法还正在加重我的淋巴水肿,6 年前我因为乳腺癌切除了左乳,左臂下方的几乎所有淋巴结都被清除了。肿胀的手臂一直不断地提醒我,我并非完全健康。这些副作用实在使我痛苦。
我决定放空自己,到我女儿家短途旅行,去纽黑文看看她和她的家人。
我登上了开往纽黑文的美国铁路公司的列车。火车隆隆响着,缓缓穿过马里兰州、新泽西州,之后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火车慢慢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火车里的灯和空调系统关闭了,所有的电力都被关掉了。
我们在全然的安静中等待着。我把肿胀的手臂放在狭窄的窗台上,窗台太高,手臂更不舒服了,但扶手又太低,也不行。又等了很久,仍然没有动静。车厢很热,我很渴,皮肤像是着了火。除了手臂疼痛外,我发现头也开始疼。
到纽黑文最终花了 7 个小时,而不是通常的 5 小时。火车进入车站时,我大声地向周围的人表达自己的不快,看着是否有人胆敢反对我的观点。我疲惫、燥热、头痛挥之不去。
当我终于见到我的女儿时,她吻了我,我用力把身体挨着她,我想告诉她,她是多么令我骄傲,看到她这么有成就,我是多么开心。
「美铁(美国铁路公司)糟透了!」这是我口中说出的第一句话。
在纽黑文的两天,我忍不住讨论我的火车旅行。「美铁糟透了!」这句话在我脑中盘旋,我对所有愿意听的人都大声地说,一遍又一遍。
正常行为中出现此类变化,通常标志着人脑中出现了严重的病变,我情绪的过激反应——愤怒、怀疑、不耐烦——都表明的额叶正经历灾难性的变化。但我没意识到这些警示信号。作为精神疾病专家,我应该比大多数人更能看出自己行为怪异。但我却没看到。我当时不知道,6 个肿瘤和它们周围的肿胀正在使我的额叶皮层丧失功能,而恰恰是大脑的这部分能够使人反省自己。
矛盾的是,我需要通过额叶皮层才能知道自己正在失去它。
我周围的世界似乎越来越奇怪,我的困惑也渐渐变成了愤怒。我的暴躁和以自我为中心困扰着家人,他们对我小心翼翼。由于大脑功能不正常,我只专注于自己的需求,对那些指示自己身上出现了严重问题的信号视而不见。
磁共振成像显示,我的大脑出现了新的肿瘤。医生说:「你知道,你参加临床试验时,脑子里有 3 个肿瘤。自上次磁共振成像之后,你的脑子里出现了 15 个新肿瘤。」
我服用的类固醇正在减少脑部的炎症,也对我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过去两个月的记忆开始慢慢回来了。奇怪的是,我无法回想起当时的情绪,回想当时的反应和感受则更加困难。
大脑有种神奇的自愈能力,能在经历各种伤害和攻击后恢复,这种能力让科学家和医生惊叹。甚至遭受严重脑损伤的患者有时也能几乎完全恢复。
尽管类固醇缓解了我脑部的肿胀,放疗正在杀死可见的肿瘤,但家人和我都清楚黑色素瘤细胞仍然潜伏在我的身体里。因此,医生增加了靶向治疗,这曾是我开始接受免疫疗法前的最后选项。
2015 年 3 月,我的肿瘤被从枕叶中摘除不久后就进行了基因检测,结果发现存在一种罕见的突变基因:BRAFA598T,只有不到 5% 的黑色素瘤中会出现这种突变。医生说我应该立即组合使用曲美替尼和达拉菲尼。
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这些新药似乎是我最后的存活机会。但这些药物并未获得 FDA 批准以用于我这种罕见的突变,我的医生便为我向制药公司争取到了「同情用药」。
7 月 21 日,新药的组合疗法成功了。医生告诉我,我的所有肿瘤的大大缩小或完全消失了,脑部也没有新病变了。
2016 年 3 月 13 日,在我第一次被诊断为转移性黑色素瘤一年多后,《纽约时报》刊载了我的文章《失去理智的神经科学家》,反响迅速而惊人。
2016 年 5 月 6 日,乔治城隆巴迪综合癌症中心举办了年度黑色素瘤幸存者午餐会,我是受邀嘉宾之一。午餐会那天下着雨,天气寒冷阴沉,乔治城大学医院的会议室里挤进了 70 多人,幸存者的年龄从 30 多岁到 80 多岁不等,几乎所有人都急于分享自己的经历:症状、诊断、治疗。
他们就像从战场上死里逃生的战士,过去的情景历历在目,可以轻松地与经历过类似苦难的人讨论他们的经历,毕竟只有这些人才真正懂得彼此。
一位摄影师为我们所有人拍照,看起来像是毕业照。我们活了下来。我们仍能正常行事或发挥作用。